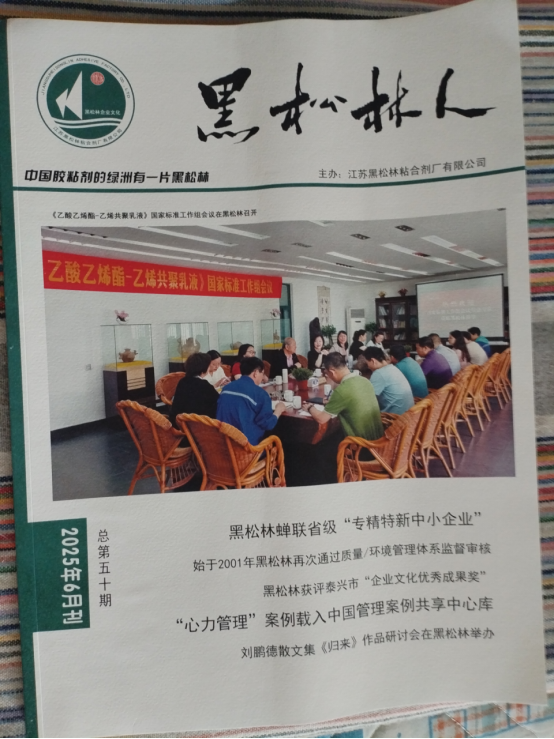导读:世界献血日之际,发送常海成老师这篇文章,很为受益!
世界献血日之际,发送常海成老师这篇文章,很为受益!
一次难忘的献血经历
常海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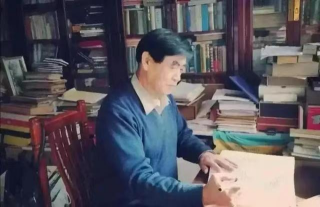
市区的休闲广场,有一辆献血车常年停在那里,每逢遇到有人献血,就勾起我的心头往事,如同昨日历历在目。在那个相对贫困的年代,我的青年时期,曾为乡人毫不犹豫地献过一次血。
我的家乡是衡水市桃城区城西南的焦汪村。记得那是1965年,我23岁。在一个天气晴朗的秋日,天近中午,干完农活,与三两乡亲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。突然,一辆标有红十字的救护车从大路上向我们的村庄急驶而去,那时脑海就挂起了问号儿,村里不知哪家有危急病人需要抢救。
天已到了午饭时分,饥肠辘辘的我,刚要走进村后街的家门,不料,那辆救护车竟向我驶来。车没等停稳,我们在一个生产队的占桐二哥就从车上跳了下来,满脸愁容地对我说:“海成兄弟,你二嫂难产,现在马上送她上医院,需要多人帮忙,你也跟着去吧!” “行”!来不及进家告诉爹娘,我二话没说就钻进了救护车。躺在车厢里的二嫂,闭着眼睛,头发蓬乱,面色苍白,几近虚脱。车上还有我们生产队的书林、占华、保春等四五个青年,没人说话,空气似乎都凝固了。救护车在乡间路上飞驰着,卷起一溜烟尘,很快就来到衡水老石桥边的县医院。我们几个合力把二嫂抬上担架,送进急救室。就在急救室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,我注意到旁边的占桐哥脸色苍白,满头大汗,几乎要晕倒。大家迅速上前扶住他,让他坐在一旁的座椅上静静休息。我们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下了一些。
占桐哥姓崔,在家排行老二,三十大几岁,身材高大,能干,有心计,说话爱拐弯,幽默风趣。二嫂是外乡人,为人朴素热情,话音不是咱家乡味儿,有时咵得让俺们都听不懂。二哥家里很穷,他十几岁去东北打工时认识了二嫂这个东北妹子,然后二嫂就跟着二哥嫁到了这偏僻的村庄里,可二嫂从没说过苦。他俩生有一男二女,这是二嫂生的第四胎,当前生命垂危,如二嫂有个三长两短,这个家可怎么过啊?我们几个年轻人在急救室外的走廊里,焦急地等候着,希望占桐嫂子平安无事。
急救室的门刚打开,我们几个呼啦一下子围了上去,穿白大褂的医生把我们引到一旁说:“产妇难产,失血过多,需要马上输血,怎么办?”跟在医生后面精神恍惚的二哥,双眼布满血丝,仿佛一下苍老了十岁,这个三十多的汉子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们几个,短暂的沉默后,我轻声且坚定地说:“我先来。”医生看了我一眼,微微地点了点头说:“好,跟我来。”医生迈着急促的步子,同去的几个人和我紧跟在医生后面,来到一个小窗口前,窗内的人让我伸出一只胳膊,用小皮筋儿捆住,在我那鼓起来的血管上吸出几滴血,这位女医生温和地说:“别急,得略等等,看血型配不配!”他们几个都围到我这里,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输血的事。
那时,我虽是初中毕业,在当时农村也算是个知识青年了,但对医学知识懂得很少。只知道血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东西,至于人的血还分型号,真没听说过。这次来医院才知道人血分A型、B型等好几种,两个人的血型一样,才能补充输进,同时知道了只有O型血是万能血,什么样的血型都能输补。当时我就盼着自己是O型血,能救二嫂就好。这时,医生隔着小窗口喊我的名字,我急忙来到近前,医生温柔地说:“你是O型血,你的血能用,你来吧!”这时占桐哥也跟着过来了,眼睛有些湿润,嘴角抽动着,好像说:“海成兄弟,救命吧!”我脑子里没有一丝犹豫,把左胳膊伸到了小窗里,医生熟练地把针头扎进我的血管,还没感觉到一点不适,一股鲜红的细流从我胳膊间沿着洁白的小长管,就流到了透明玻璃瓶内。
在那个卫生科学尚不普及的年代,大都对人体内的血具有神秘感,村里有些迷信的老人不让照相,说照相吸人身上的血不好。若把手划破一道,流点血还又痛又怕,更何况现在从体内向外不停的抽血哩。当时,可能是心理作用吧,真的有点慌乱。但那时正是红色年代,“老三篇”都能熟背下来,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都培育成赤诚的青年,时时处处想的就是多做好事,平时哪怕看到路上有牲口粪,我都要想法弄到集体地里作肥料。现在在这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,出点血又算得了什么!看着大瓶内的血在慢慢增长,我的心异常平静,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守护我的村友,让我闭上眼睛,思想放松,我向他们微微一笑,说:“没事没事。”
过了一小会儿,医生拔出针头,让我用手按着棉球压住针眼儿。当时除了针眼有点疼和一个姿势的手有点麻木外,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。输血结束后,占桐哥领我来到二嫂病床前,看到高高的支架上吊着一个大瓶子鲜血,正顺着一条长长的软管,一滴一滴流向二嫂的血脉。医生告诉我:“输了您300CC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病床上的二嫂见到我,下意识地看了看那瓶中的鲜血,又好似感激地看了看我,嘴角微微地动了动,说了些什么,我没听清楚。看到精神逐渐好转的二嫂和在她身旁那个虎头虎脑的小宝宝,我心里无比舒畅,高兴地退出了病房。
县城离我们村有35华里,不知谁弄来了一辆自行车,二哥与队友们非让我骑着走,我觉得心里热乎乎的,因为他们步行回家需要4个多钟头。我骑车出了县城,路过大庙村与旧城塔,穿过北沼、南沼、种高村,用了一个半钟头骑到村口。这一路说不累是假话,总觉得腿脚有些发软,头也有点飘悠悠的,但想到二嫂母子平安,感觉这些付出都很值得。
进了村里,心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,琢磨着回家如何向家人交待呀。当时我结婚刚一年多,妻子在她娘家巨鹿村教学,每到星期天来家里与我推碾子,碾出些米面够吃六、七天的,就又回娘家给学生上课了。妻子正好不在家,倒是好瞒过,只是怎样对年迈的爹娘说呢?二老对我疼爱有加,偶尔炒个鸡蛋做个差样的饭菜,还总往我碗里夹,说我干活累,得多吃点。这次输血若让二老知道,还不知多心疼哩。为使二老心理上有个缓冲期,我想还是暂不把输血的事告诉他们为好。因对这件事想得太投入,骑着车子差点撞到路边那棵歪脖树上。
我装作没事一样,故做轻松地进了家门,爹开口就问占桐家怎样了,我报了平安,爹松了口气,埋怨说:“你走也不说一声,叫人惦记着。”娘递给我一碗白开水,说:“出去一天了,再年轻也不能这么折腾,快歇会儿吧。”这时才觉得嘴唇像开裂的痛,我咕咚咕咚地喝了水,就借坡下驴说:“是累了,我睡会儿。”以往我干活或外出回来,娘总让我躺在炕头上,这次我爬上炕头,娘给我盖上被子,开始我脑子很乱,睡不着,那根流淌着鲜血的细管子老是在眼前晃,可能是真累了,一会就呼呼地睡着了。吃晚饭时,娘才叫醒我,这时肚子确实饿了,我大口吃着高粱玉米面两掺的饼子,蒙在鼓里的爹娘看到我这个吃劲儿,乐呵呵地说:“行,能吃就能干。”
第二天上午,我去上工,队里没派我下地干活,让我回家休息,娘问:“今天怎么不下地了?”当时我有在墙上不用划格就能写仿宋黑体等大字标语的特长,大队里、公社里常找我去干这活儿,我说:“有人找我写大字标语哩!”这样又瞒过一回。
歇了一天,我又狠狠地睡了一宿。就在这天早起,爹不声不响地将一只老母鸡杀了,娘红着眼圈生起煤火炉把鸡炖上,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,一看这像似过年的来头儿,我知道献血的事爹娘知道了。这时占桐二哥也来了,他提着一块猪肉和一篮鸡蛋,对我爹娘说:“大叔大婶,多亏俺海成兄弟救了小黑他娘一条命(小黑是占桐的大儿子),这点东西给俺兄弟补补身子。”爹是厚道义气人,说:“占桐,咱乡里乡亲的过得着,就是遇上外人,也该这么办。”娘直白地说:“小黑他爹,你怎么不早说呀,海成这个小子直到现在还没跟俺们说哩。只要小黑他娘大人孩子都好好的,俺们就放心了,你快忙你的去吧,甭挂心了,这不我正给他炖鸡哩。”说着不知怎的,爹娘都不自觉地落下泪来,二哥和我眼睛也湿润了。
时光荏苒,一些人和事都淹没在岁月长河中,这件事虽然过去了近六十年,但在记忆中依旧清晰。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,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爱尤为珍贵。而这一切,皆得益于爹娘平时言传身教的无形浸润,根植于淳朴敦厚的好家风、民风赓续传承,更来源于那个年代红色教育对灵魂的深刻洗礼。
当年我的一次小小善举,不仅挽救了两个生命,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情感,同时还转变着村民对献血的看法。如今休闲广场的献血车常年停在那里,看到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,我十分欣慰。愿世间真情大爱如涓涓小溪,汇成江河,任岁月更迭,源远流长!




2002年5月25日初稿
2025年6月2日成稿